病历记录“笔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发布时间:2012-12-25来源:发布者:浏览次数:773打印本页
病历记录“笔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浙江颂阳律师事务所 李颂
[裁判摘要]
病历资料,是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以书面形式或电子数据形式对患者的症状、医学检查、诊断结论和治疗过程及效果等情况所作的记录,也是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活动是否存在过错进行综合评价的最重要依据。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病历资料,必须保证病历资料内容的客观、真实、完整。医院在病历记录上存在多处矛盾及不合理之处,使患者对病历的真实性以至抢救措施的及时性、规范性产生合理怀疑,医院对此仅仅解释为“笔误”,显然难以让人信服。因病历记录中存在的问题导致医院对患者实施的抢救措施是否适当等事实难以查清,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医院承担。
[关键词]
医疗损害 病历记录 赔偿责任
[案情简介]
2010年9月8日上午5时许,患者李某因“胸闷1小时”到当地人民医院(以下称为“医院”)就诊,按医院要求进行心电监护、胸片、心电图、血常规、心肌酶+肌钙蛋白、D-二聚体检测等,被当值医生诊断为“胸闷待查”,给予药物点滴治疗。6时,李某胸痛加剧,突发面色青紫,心跳骤停,医院组织抢救无效,于同日上午7时35分被宣告死亡。
李某的病历显示:“6:00 胸痛加剧 突发面色青紫 心跳骤停 心电监护HR 0次/分 SPO2 100% CPR肾上腺素针1mg iv st ”、“6:10 CRP 电击除颤 HR 0次/分 SPO2 100%”、“ 6:15 CRP 肾上腺素针1mg iv st HR 0次/分 SPO2 100% 电击除颤”、 “6:20 CRP 电击除颤肾上腺素针3mg iv st HR 0次/分 SPO2 55% 请心内科医师会诊 请麻醉科医师会诊”、“6:30 电击除颤1次 NS 250ml 肾上腺素针10mg iv st”、“ 6:30 急性心肌梗死需考虑”(心内科医师)、“CRP 呼吸机辅助通气”、“ 7:35宣告死亡”。
经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检验,李某“因重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伴斑块内出血及血栓形成,出现泵衰竭,导致心源性休克死亡”,“主要病变为心脏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其中以左旋支主干的病变最严重,阻塞血管腔85%以上”。据此,医院拒绝了李某亲属提出的赔偿申请。
2010年12月14日,李某亲属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李某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死亡为由要求赔偿经济损失67.5万元。人民法院受理后,根据医院提出的申请,委托了宁波市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技术鉴定。2011年6月22日,宁波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书》分析意见认为:如果根据病历记载、辅助检查、尸体解剖结论以及医方陈述,该医疗过程符合诊疗常规,急诊处理过程中医方已给予患者包括吸氧、除颤、呼吸机辅助通气等措施,不构成对患者的人身医疗损害责任。但患方对病历上记载的关键治疗措施,包括除颤、呼吸机辅助通气等均予以否认,故无法得出鉴定结论。
2011年11月,当地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病历是记载医院治疗过程的最主要证据,应当推定病历记载反映了抢救治疗的全过程。同时考虑到,病历是由医院单方面形成的并允许补记,为了实现医患之间的利益平衡,法院对于病历记载的内容对医院方面应该从严审核。病历中未记载或者记载不全的,应对医院作出不利解释。根据现有病历记载,医院无法证明自己在使用呼吸机前使用过其他辅助呼吸手段,也无法证明自己适时除颤,应认定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本案中医院的过错行为和病人自身病情共同作用导致了最终的损害结果,法院应当根据医院过错行为对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来确定赔偿范围,认定其承担50%的赔偿责任。据此,判决医院赔偿给李某亲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35083.75元。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不服判决,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李某亲属上诉称,医院病历明显存在伪造,应当依法推定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且一审判决未能认定医院的明显过错,要求改判医院赔偿全部经济损失。医院上诉称,病历记录有瑕疵,是抢救过程中情况紧急“笔误”所致,医学会鉴定结论已肯定医院抢救过程符合医疗常规,一审不予采信是错误的,要求改判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
2012年4月6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观点]
患方(李某亲属)认为,医院伪造病历,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而且根据病历记载医院存在重大过错。主要表现在:
1.未进行持续心肺复苏。病历记载中除了“6:00”采用了“CPR”,后面的“6:10—6:30”均采用“CRP”。 “CPR”也叫心肺复苏,是抢救病人最常用的措施;但是“CRP”在百度百科里的定义是“机体受到微生物入侵或组织损伤等炎症性刺激时肝细胞合成的急性相蛋白”。显然,根据病历记录,医院只有在“6:00”对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之后没有进行过心肺复苏的抢救,那么患者怎么可能不死亡?
2.没有肺复苏治疗的记录。病历记载中不论是“CPR”,还是“CRP”,其后面仅仅记载“电击除颤”,而“电击除颤”只是心复苏措施,“电击除颤”不可能让肺复苏。医院既然在病历中记录了心肺复苏的抢救措施同时写明了心复苏的具体措施,那么不可能不记录肺复苏的具体措施;既然病历中没有记录肺复苏的具体措施,只能认为没有采取肺复苏的具体措施,心肺复苏名不符实。
在医学鉴定过程中,医院认为采取了呼吸机辅助呼吸等肺复苏措施,但患者亲属予以否认。况且,使用呼吸机需要麻醉医师进行操作,但是病历中只有通知麻醉医师会诊的记录,没有麻醉医师会诊结果的记录,可见麻醉医师自始至终没有参加抢救,怎么可能对患者使用呼吸机。
3.连续“电击除颤”依据不足。医学上对心跳骤停的患者允许进行首次盲目除颤,以后应该根据除颤后的心电监护,判断是“室颤”还是“停博”,只有是“室颤”的情况下,才能再次进行除颤;如果是“停博”,进行再次“电击除颤”反而造成心脏损害。医院在“6:10”进行首次盲目电击除颤后,并无记载除颤后的心电监护数据用以断定是“室颤”还是“停博”,此后连续进行多次“电击除颤”明显依据不足,可能造成患者死亡结果发生。
4.病历记录中“HR 0次/分 SPO2 100%”自相矛盾。“HR”也就是心跳次数,“SPO2”是血氧饱和度。在心脏骤停,心跳0次/分的情况下,患者血液内的血氧饱和度是不可能达到100%的。这是医学常识,医院在诉讼过程中也自认这一点。但是,病历中从“6:00”— “6:15”出现三次“HR 0次/分 SPO2 100%”的记录,令人难以置信。
病历本身还记载了患者“面色青紫”,这明显是缺氧、血氧饱和度不足的表现,医院却还是记录“SPO2 100%”,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而且,病历中并没有给患者进行吸氧的记录。
5.大剂量药物静脉推注,可能促使患者死亡。病历记录显示“6:30 NS 250ml 肾上腺素针10mg iv st”中“ iv st”是静脉推注的代号,而250 ml的NS加上10mg的肾上腺素针,如此大剂量的药物采用静脉推注的方法,就是连正常人也是难以承受的,更何况是心脏骤停的患者。因此大剂量药物静脉推注,可能促使患者死亡。
医院认为,宁波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足以证明医院“不构成对患者的人身医疗损害责任”,虽然病历记录中存在如“CRP”、“HR 0次/分 SPO2 100%”、 “ iv st”等矛盾,以及除颤后的心电监护数据、呼吸机辅助通气、麻醉医师会诊记录等遗漏,都是抢救过程中在所难免的“笔误”。
[争议焦点]
一、病历记录中的差错,到底是不是医院的“笔误”,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二、医学会的分析意见是否准确?医院对于患者死亡是否有过错?
[法院评判]
一审法院认为:医院在对患者抢救过程中应当同时实施心复苏和肺复苏两种手段。病历上在“6:20—6:30”这个时间段里记载了请麻醉科医师会诊,表明急诊医生没有能力独立完成呼吸机插管。即便事后补记的呼吸机辅助呼吸属实,病历上对于使用呼吸机之前是否还使用过其他人工辅助呼吸手段未作记载。在电击除颤过程中,病历中只记录了心跳、血氧饱和度等指标,没有记载血压,也未附有心电监测图。心跳为0,只能表明病人失去自主心跳,不能反映在实施心脏按压之后,在心电监测图是否出现颤波。如果在无颤波的情况下进行多次电击除颤,反而对病人不利。根据现有病历记载,医院无法证明自己在使用呼吸机前使用过其他辅助呼吸手段,更无法证明自己适时除颤,应认定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但急性心肌梗塞是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所以医院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医院在病历记录上存在多处矛盾及不合理之处,使患方对病历的真实性以致抢救措施的及时性、规范性产生合理怀疑,医院对此仅仅解释为笔误,显然理由不充分。因病历记录中存在的问题导致医院对患者实施电击除颤是否适当、在使用呼吸机之前是否使用过其他人工辅助呼吸手段、对患者采用何种方式输入250ml药物以及心电监护的具体数据等事实难以查清,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显然应当由医院承担。鉴定报告认为如果病历记载、辅助检查、尸体解剖结论以及医方陈述,医院在急诊处理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但该意见的客观依据显然不足,且难以排除医院的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根据患者的尸检报告及就诊时的情况,患者自身病情较严重进展较快,患者自身病情也系其死亡的重要原因。综合考虑医院医疗过失行为对于患者死亡的原因力大小、患者自身疾病情况、医疗科学发展水平、医疗条件等因素,原审法院酌情判令医院承担50%赔偿责任基本合理。
[法理分析]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举证责任
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有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医疗损害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患者毫无疑问处于弱势地位,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缓解了患方的举证难度,对维护患方的合法权益起到了较为积极地促进作用。
但是,《侵权责任法》出台以后,根据该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医疗损害责任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从举证角度而言,原则上应由患方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方可能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和上述最高院的证据规定有着重要区别,实质上是加重了弱势群体的法律责任。
同时,《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二)、(三)项列举了“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二种情形(该条第一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一般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归结到本案,一、二审法院对患方提出的医院伪造病历,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过错推定原则的主张,未予明确采信,其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二、医院为自己在病历资料中的错误买单
连医院自己都认为,病历资料中内容有错误、有遗漏、有矛盾,但就是不认为自己有过错。法院的判决思路是,病历资料是医院写的,其中的错误也是你自己造成的,既然医院对自己在病历资料中的错误解释不清,就判决为自己在病历资料中的错误买单。这在一审判决理由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病历是记载医院治疗过程的最主要证据,应当推定病历记载反映了抢救治疗的全过程。同时考虑到,病历是由医院单方面形成的并允许补记,为了实现医患之间的利益平衡,法院对于病历记载的内容对医院方面应该从严审核。病历中未记载或者记载不全的,应对医院作出不利解释。
法院的上述判决思路,还是按过错责任原则来分担举证责任的,只不过是用医院自己的病历资料这份证据,来证明医院本身的过错罢了。病历记录中存在的问题导致关键事实难以查清,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显然应当由医院承担,就好像《合同法》中格式合同内容存在歧义要由合同提供方承担不利后果一样的道理。
如果把如实书写病历资料、把应该书写的诊疗措施不加遗漏地记录在病历资料理解为医务人员的诊疗义务之一,那么对法院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的规定,判定医院承担责任,似乎更能让人理解。
三、病历记录“笔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所谓“笔误”,是指因疏忽而写了错字,也指因疏忽而写错的字。针对病历记录中的种种矛盾和错误、遗漏,医院就是以“笔误”进行解释的。
但是,“笔误”显然难以掩盖事实真相:患方当庭要求医院解释,病历中的“HR 0次/分 SPO2 100%”如果是笔误,那么到底是“0次/分”笔误了,还是“100%”笔误了?假如允许更正的话,应该是多少?病历中出现一处“笔误”似乎情有可原,但是连续出现三处同样的 “笔误”令人难以想象。
面对患方的诘问,医院显然不能回答。因为这个错误根本就不是“笔误”,“笔误”是有正确结果,而且下笔时是明知的,但是本案中医院根本没有当时心跳次数、血氧饱和度的原始数据,自然是没有正确结果,也不可能知道结果的,所以即使允许其纠正也难以得出正确数据。
患方也正是基于这个事实,主张医院伪造病历。所谓伪造,就是假造以欺瞒别人,就是无中生有。由于医院根本没有准确数据,在病历上的数据根本不可能真实,完全是医院欺瞒患方的不真实的记录。
按照患方的主张,医院伪造病历资料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推定医院有过错。一、二审法院对此显然讳言莫深,轻易不敢触碰;但是,一面是鲜活的生命,一面是冰冷的“笔误”,在审判者内心或许早已有了“笔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上一篇:没有啦!
下一篇:没有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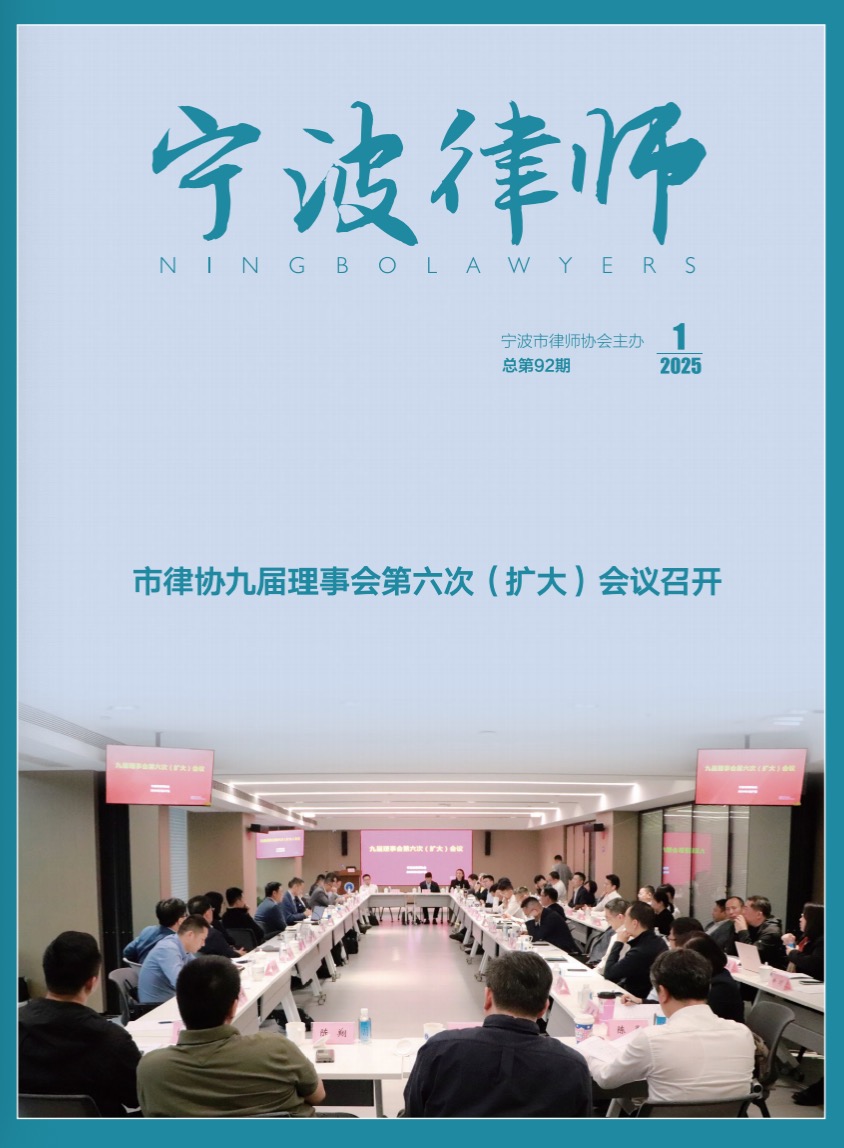




 扫码关注
扫码关注
